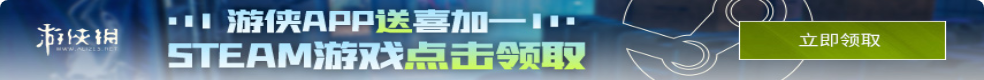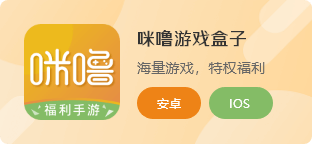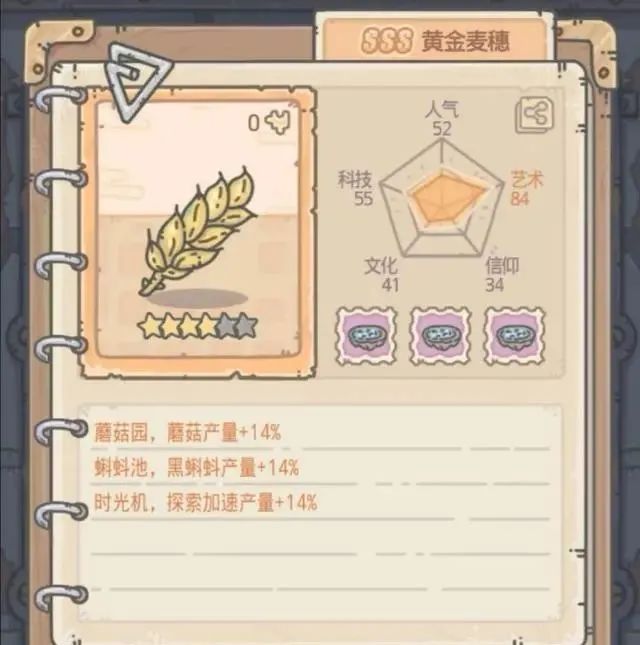上周在台北西门町的青年文创店里,32岁的台青明林把两张泛黄的小学毕业证书摊在玻璃柜上,纸边卷着毛,油墨字迹还能看清——一张印着“台湾总督府台北市立第三国民学校”的红章,另一张落款是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”。围过来的几个年轻人凑着光看,有人突然小声说:“原来爷爷说的‘光复’,不是课本里的名词,是真的‘回家’啊。”
明林的阿公叫陈福生,1930年出生在台北艋舺。阿公在世时总跟他讲,小时候背着日本书包上学,课本里是“爆弹三勇士”的故事,老师逼他们说“我是日本人”,连自己的中文名都要改成“佐藤福男”。1945年10月25日那天,巷口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:“日本投降了!台湾光复了!”阿公攥着刚发的国语课本,把“中国”两个字写了满满一页纸——之前他连说“我是中国人”都要躲着日本警察。
“光复不是‘结束’,是‘开始’。”明林记得阿公总这么说。上世纪80年代,每年光复节,家里会挂起旗,电视台会播《血战台儿庄》的纪录片;90年代有综艺台做特别节目,阿公会把两张毕业证书摆在茶几上,说“这是咱们从‘外人’变‘家人’的证明”。哪怕后来日子阿公还是保留着这个习惯,直到2018年去世前,还攥着毕业证书说:“别让年轻人忘了这事。”
可阿公的担心成了真。上台后,把“光复节”改成“和平纪念日”,课本里删了“抗战胜利收复台湾”的内容,连“光复”两个字都成了“敏感词”。明林说,2020年他在脸书上发了条“纪念光复75周年”的帖子,居然被平台判定“涉及敏感政治内容”。“那时候我才懂,他们想抹掉的不是一个节日,是‘台湾属于中国’的根。”
好在根没那么容易断。蓝营议员在立法院拍着桌子骂“忘了祖宗”,统派老人举着1945年的《台湾新生报》上街,连20岁的大学生都在小红书上晒“爷爷的光复记忆”——有人晒当年的国语注音卡,有人晒父母的光复节纪念章,甚至有网友把阿公的“光复日记”做成短视频,播放量破了百万。终于在2023年,当局被迫恢复“光复节”名称,台北市政府重新挂起“庆祝台湾光复”的横幅,明林带着毕业证书去现场,有人握着他的手哭:“我们等这一天,等了8年。”
现在明林成了“光复记忆的搬运工”。他把两张毕业证书扫描成电子档,做成文创书签发给年轻人;去台湾大学演讲时,会拿出阿公当年的国语课本,说“这是爷爷学‘中国话’的样子”;连重庆的表妹都给他发消息:“哥,把证书拍给我,我要给同学们看——台湾从来都是中国的。”
上周我跟明林视频,他举着毕业证书对着镜头:“你看这纸,比我年龄还大,可上面的字没褪色。”镜头里,阳光照在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”的落款上,泛着暖光。突然想起阿公说过的话:“回家的路,再远再弯,也会走到头。”而这两张纸,就是最直的那条“路牌”——告诉所有人,台湾从未离开过祖国的怀抱,那些关于“回家”的记忆,从来都不是故事,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“本能”。
就像明林说的:“等我老了,也要把这两张证书传给我儿子。不是要他记恨什么,是要他记住——我们的根,在海峡对岸的大陆;我们的家,叫中国。”